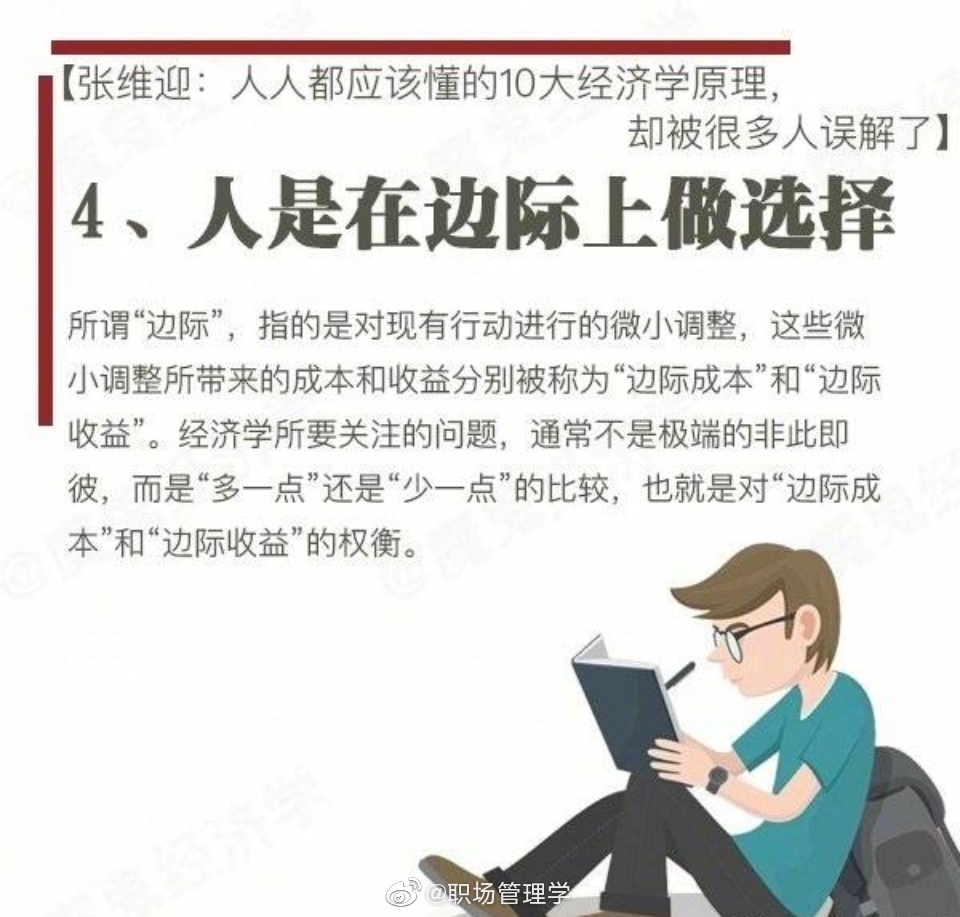“雇佣兵既无用又危险。”五百年前,Machiavelli这样警告过。然而在21世纪,私人军事公司——这个现代化的委婉说法——却迎来了新的繁荣。
战争带来苦难,也制造需求。今年早些时候,加沙人道援助基金会在执行任务时雇佣了美国的UG Solutions提供武装护卫。俄罗斯则依赖由前特种兵组成、克里姆林宫支持的瓦格纳集团,为其在乌克兰与非洲的行动提供人力。哥伦比亚雇佣兵甚至也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。而在西方,美国政府依旧是私人军事公司的最大客户。
这个行业的跨度极广:从商场保安、企业武装警卫,到真正上战场的“战争承包商”。他们多为退役士兵,尤其是特种部队成员。过去二十年,随着各国政府削减军队规模,民间安全需求猛增,这一产业悄然扩张。如今业内人士热切期待乌克兰战后重建,希望它像伊拉克那样带来下一轮商业盛宴。
上世纪初的伊拉克战争是这个行业的黄金年代。前英国军官Tim Spicer回忆,当年伊拉克遍布数万名承包人员,其中大多数并不直接参战。战争结束后,大批“牛仔式”小公司涌入,但如今行业早已形成成熟的企业化格局。几家大型公司拥有完整的法律、合同、人事体系,如美国的Constellis(年营收14亿美元,员工逾1.2万人)和加拿大的GardaWorld,业务遍布数十国。
分析师Dominick Donald指出,市场大致分为两类:一类是资金雄厚、背靠风险投资的正规公司;另一类则是处于“休眠状态”的小型承包队伍,一旦有大单出现,往往被前者收购。
退役伞兵、现任学者Sean McFate把这个行业分成三大阵营:英语系(主要来自美国与欧洲)、俄语系,以及西班牙语系(多为拉美与哥伦比亚的前特种兵,他们常受训于美军“绿色贝雷帽”)。每个阵营都有独特文化与作战风格。
随着各国征兵困难,私人武装成了低成本替代。Spicer透露,一名美国合同兵的成本仅为正规士兵的七分之一,而英国雇佣兵更便宜——约十分之一。哥伦比亚人力价格更低,“他们的薪酬只相当于我当年四分之一。”McFate说。
但对雇佣兵本人而言,这依然是一份“好工作”。哥伦比亚人受雇后收入远超本国军官,还能住上更舒适的营地。乌克兰的俄籍雇佣兵一度拿到正规军两倍薪资。然而金钱并非唯一动力。McFate指出,许多人选择这行,是为了“掌控自己的命运”——他们可以拒绝被派遣,这种自由让人上瘾。
虽然多数私人公司不直接参与正面战斗,但过去十年出现更多所谓“作战解决方案”的提供者。利物浦大学的Ulrich Petersohn统计,乌克兰战场上曾有五万多商业武装人员,多数技术低劣,尤其在俄方阵营,用以替代正式征兵。
Spicer抱怨“雇佣兵”一词被污名化。他认为,像瓦格纳那样的准军事集团受专制政府庇护,玷污了整个行业。而研究显示,从1980年至2016年,雇佣兵参与冲突的地区,平民伤亡率平均下降39%;若公司来自民主国家,这一比例降幅高达66%。换言之,越“企业化”的武装组织,越有动力遵守规则。
当然,西方公司也并非无瑕。加沙的人道援助项目中,就曾出现雇佣美国极端摩托帮“Infidels Motorcycle Club”的丑闻;而Erik Prince——那家臭名昭著的“黑水公司”创始人——旗下的Frontier Services Group因培训中国飞行员而在2023年遭美方制裁。
如今,越来越多业内人士认为,新的雇佣兵浪潮正在逼近。Spicer直言:“乌克兰的战后重建将让伊拉克的经历显得微不足道。”
未来的市场人力几乎不成问题。乌克兰战争将留下成千上万具备无人机和电子战经验的老兵;总统Zelensky甚至计划设立本国的私人军事公司。与此同时,许多美军精英在喀布尔撤离后结束休整,准备投入新任务——从打击拉美毒枭到保护稀有金属矿区,他们将成为“商业化战争”的主力军。
McFate总结得冷静而锋利:“战争的私有化已无法逆转。理解它的人,如俄罗斯,正主动拥抱;拒绝它的国家,可能会被迫学习。”
也许,未来的战场不再有国旗。只有徽章、合同,还有那些被重新定义的士兵——为雇而战,为利润而生。